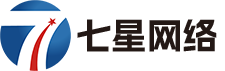“又见炊烟升起,勾起我回忆。愿到我梦里”。随着时间的流失 和青春的消逝,很多记忆如陈年佳酿已被尘封。只是,从未曾忘记皖北故乡夕阳下的那一缕缕淡淡的炊烟,在心头眼底悄悄氤氲开来。
儿时的皖北农村,家家厨房的灶都是用砖砌成的,靠近墙壁处树立一个烟囱直上屋顶,灶的边上会放置一个用木材制作成的木箱,用于烧柴火或者烧煤炭时增风加大火焰时使用。俗话说有炊烟的地方,就有村庄,就有生活。炊烟在召唤着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及时回家,家家屋顶升腾炊烟里也蕴含着生活酸甜苦辣的味道。那时候,经济条件不好,生活清苦,中午放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厨房,帮着母亲烧火做饭,有时候也会帮着父母拉风箱,父亲烧火,母亲做饭。在老式风箱不断重复的“吧嗒”、“吧嗒”声中,那些柴草和劳累化成了希望的炊烟,不断从烟囱中升腾,直到炊烟越来越淡,最后消失时,父母的饭菜就做好了,一家人围着灶台说说笑笑度过贫苦的生活。当然也有时候,会在下午放学后背着一个柳条篓去割青草,用来喂家里养的牛羊和长毛兔。本来放学时就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,就渴望能早点割好回家,每当远远看到村庄浓浓的炊烟升起,就知道妈妈已经开始做饭了,心中倍然增加了希望和温暖。隔着小河、隔着村野,隔着田里的庄稼,仿佛就闻到了家的味道,看见了母亲期盼的眼神,催使自己加快步伐,朝炊烟升起的家里赶去。
后来,为了理想打拼离开家乡20多年,早已习惯了城市朝九晚五的生活,习惯了城市里干净的厨房和现代厨房电器,钢筋水泥楼房建筑里再也看不到袅袅升腾的炊烟,却忽然发觉平凡的生活少了很多烟草的味道,一日三餐里不见了父母和亲人相聚的味道。前几年和爱人一起回到生我养我的皖北老家,农村的发展天翻地覆,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,农业规模化、集群化初见成效。原先的村庄由于受采煤塌陷,村庄重新进行了规划和搬迁,老村一片狼藉、残垣断壁。站在我出生并生活了10多年的老房子前,厨房的墙壁已经被烟火熏得发黑,风箱也早已不知去了何方,唯有院墙前的那颗老枣树还在孤零零的站在那里,静静地诉说这一切的过往。弟弟说,村里大部分基本都已经搬到新村,留在庄里的也只有几家老人了,过不了几年,老庄也将不复存在,将要统一恢复成一片庄稼地。作为一个农村人,我没曾见过生我养育我的村庄的诞生,却目睹了它的日渐消亡,永不了几年,所有儿时的回忆,萦绕在梦里的乡愁,全都不复存在。其实我知道,每个人,每一生,都会遇到太多的不舍,太多的离别,太多的坎坷,到最后多半也只是屈从于现实的无奈而已。但是这一生太长,心动太短,故乡的炊烟,梦中的乡愁,其实已经渗入到骨子里。不知故乡的那一缕炊烟何时再能升起,愿不远的将来故乡不仅在梦乡,它有诗,有梦,有绿水青山和炊烟袅袅的远方!
有人说炊烟是家乡的味道,那里有泥土和着庄稼桔杆的气息,瞬间蓄满心田让人温暖;有人说炊烟是童年的记忆,那里有父母家人的笑脸,一家人围在灶火房,一日三餐品尽生活冷暖;也有人说炊烟是希望和方向,“山上层层桃李花,云间烟火是人家”,山穷水尽时,炊烟是柳暗花明的豁然开朗,让困惑的你找到奋进的希望方向;我要说,炊烟是一种人生的态度,炊烟是人间烟火,是生命的衍息地。袅袅升腾的炊烟中,鸡犬相闻,呼唤声声,柴草、灶膛和风箱的结合成就了粗茶淡饭和美味佳肴,而炊烟则轻轻地挥手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不正是一种欲说还休,欲罢不能,拿得起却放不下,剪不断却理还乱的乡愁?它把岁月干涸的柴草丢进烈火燃烧的灶膛,燃起一股粉身碎骨的思念之火,升腾起一股股魂牵梦绕的牵挂之烟,飘向乡村城市、飘向遥远天际、飘向每一位思乡游子的梦中
故乡的那一缕炊烟,因人而聚、因家而生,因爱而暖,像一根长长的青丝带,一头飘摇在故乡的上空,一头系在走出了故乡的儿女的心上,生成了根、凝成了绳、结成了迦、汇成了梦……
作者简介:
张琳,安徽濉溪人,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、诗歌委员会委员,鲁迅文学院国土资源文学创作班学员,云南省网络作家分会理事,普洱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、副秘书长,云南云联盟特约撰稿人,中国自然资源诗群、地学诗歌副主编。近年来发表各类新闻、文学作品500余篇,作品获中国徐霞客诗歌散文奖,出版《留恋这身绿》《穿过普洱茶香的城市》《我在茶城等你》《穿过山野的风》(合著)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