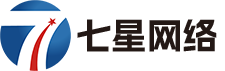二叔带我去老街里的文化宫看电影,电影的名字《枫树湾》,演到半截停电了,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往回走,二叔问我,最近有啥心愿?我说,我想要一杆红缨枪,消息树下站岗小八路的那种红缨枪。大雄有支木驳壳枪,谁跟他表示友好才让拿在手里玩玩。
二叔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,好好念书,红缨枪的事交给二叔了。
两个月后,我远远地看见二叔,一只手扶把骑着自行车,另一肩上扛着一杆红缨枪。那支枪精致得超出了我的设计想象,虽然枪头也是木头的,但那细长八面菱角打磨出了金属的质感,比舞台上灯光下的红缨枪还要炫目。
二叔指着枪头说,这是马村路边死了棵枣树,又捋着枪杆说,这是革命路菜窖里向外扎白菜的钩子断的把,白蜡杆的,韧性真好。
这支枪被我藏在了靠墙的褥子底下,在我看来,它还没有完工。红缨枪,红缨红似火,枪头放银光。缺少画龙点睛的红缨缨,就像战士没戴军帽,缺少应有的威武。
“绒劈”其实就是毛线,是扎辫子用的红头绳。大地商场的一毛,线团小一些,绑枪缨缨也足够了。那时一个学期学费一块一,一毛钱是笔“巨资”。下定决心向奶奶开口,奶奶说,你要是买糖吃,立马偷着掏给你,一毛钱的绒劈,够你妹妹梳好几年辫子,你绑个大枪,这个道理上说不过去。
奶奶虽然没给我钱,但帮我完成了那支红缨枪。
下放到镇上的老右常年穿一件脏旧的中山装,他对我奶奶极其尊重,总是站稳了再叫大娘,从不像别人匆匆敷衍打招呼。我偷听过老右哼京戏,不像“提篮小卖拾煤渣”那般流畅,是春水绕松的感觉,柔婉又挺拔。
老右把我叫到他的“牛棚”,听大娘说,你二叔给你做了个红缨枪还差缨缨,老右递过一团黑白缨缨穗,这是我唱戏用的胡子,马尾的。我摇摇头说,这个不行,八路的驳壳枪把上栓红绸子,红军草鞋上是红缨缨球,黑狗子的枪才是这色。老右咧嘴笑了,你知道红缨枪的“缨缨”干嘛用?老右说,首先是挡住枪头的血,血流到枪杆上手打滑,所以这缨缨又叫“血避”,最好是牦牛毛,不沾水,血一抖就掉,另一个作用就是迷惑对方,红缨舞动能看出武功的高低。
几天后我放学,黄昏中远远看见老右站在门口的台阶上,伸直了右臂,手里举着一团红彤彤的缨缨穗。帮我绑扎好后,老右单手抖了一下我的红缨枪,那缨缨抖成个突地张开的雨伞,我相信诚如其所言,红缨能看出功夫高低。
我的红缨枪出世后,立刻招来众多羡慕目光的小伙伴,大雄好几次低头看端详自己的驳壳枪,很长一段时间,我扛着那支红缨枪,后边跟着一堆岁数相仿的孩子,成为小镇上一道风景。
许多年后拨乱反正,我坐在灯光黑暗的电视机房里盯着那雪花飞舞的黑白荧屏入神,那里面,林冲夜奔。我蛇咬了一样从马扎上噌地站起来,从心最柔软的地方涌出了一句深情呼唤:老右叔叔……
此时我心里也有一杆枪飞舞,那缨缨是猪血染红的髯口。
好景不长。有一次中午玩打仗游戏,兴头上忘了时间,十几个人迟到,武器全被老师没收。大雄和他爷爷晚上去马老师那讨要他的木枪,马老师说,拿走,别再来上学了。祖孙二人讪讪而归。
二叔听说红缨枪被老师没收后说,好好念书,马上恢复高考了,考个中专生,别老惦记当赤卫队长了。
再次见到那支红缨枪我已经在县城读初中,我把偶遇买储藏白菜的马老师送回家,帮她往小房抱白菜时,看见了戳在墙角我的红缨枪,枪杆上长满老年斑,那缨缨已是黑白色。青埂峰一别,已数载矣。为此,我心里钮了梁子,好多年没去看望马老师。大学寒假远远瞄见马老师背影,双手抱闸单脚点地,拐自行车绕行问津街了。
(祁 文/文 刊于燕赵都市报2018年6月12日第21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