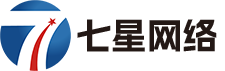一个雾霾的清晨,我去上课,路上一个孩子和他的妈妈打我身旁过,孩子很是好奇地问妈妈:天有多高啊?我已然从他们身边走远,隐约听得妈妈说,天,很高的……
疏忽间,想起自己小时候,应该也问过大人同样的问题吧,记不得大人怎么回答的。而大了之后则再也没有纠缠这个问题。也不知道自己是找到了答案,还是更多的关于天地人的问题使我困顿其中,忘记了我最初想看的天。
天,有多高?是不是我们此生能够到达的彼岸?女儿有段时间,不断把这个问题抛给我,也抛给自己。她还不断问,妈妈我为什么要读这所学校?告诉她,这只是暂时的,你将来要走出这片天地的。而属于她的那个天,在哪里,通往天外的路,在哪里,我没有答案。让我疑惑的倒是,是否很快她亦如我当年,不再纠缠“天有多高”的答案,终有一天,她的天,比我的天,更快地变换,更快地定格,在童年的记忆中。
天有多高?想来那个孩子要的也并非一个数字,坐地日行八万里,巡天遥看一千河?不是,孩子的天,只是一个影像,抬头看到的那个很高很高的云气雨气雾气——哦,应该叫雾霾吧——凝结的影像。手里的风筝能不能到达?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在不在上面挂着?这个天,是顾城和李白的,是逝了的老舍的,济南城仍在,京城的我们,看也懒得看天一眼,像极了一副被错涂了色彩的画。而女儿的天,当如她脚下的路。固然不知道最终能走多远,可是当我们给她描绘塞纳河的美丽,莱茵河的风光,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的时候,她眼中浮起了艳羡的目光,我知道,
她的天,远了,她的路,也明晰了一些。
而我的天呢?或许是自己,或许是祖先飘忽不定的魂魄,或许,就只是妈妈日渐瘦消的身躯、爸爸渐渐迟缓的步履?我的天与地,曾经很远,我的天与地,如今就只有爸爸的一步间!原来,天与地,疏忽近,疏忽远,疏忽明白,疏忽混沌,我们,便在其中,疏忽生,疏忽死。
天有多高?天不知道,云,不知道,我,也不知道。
天有多高,我不想知道,云,不想知道,天,更不想知道。然,小孩子想知道,就告诉他们,天,很高很高,象那位妈妈说的。